|
“
今日大年初一,你若不是旅行过年者,“读两本游记”也是极好的。
” 
读两本游记
文|王佐良
(原载《读书》1991年6期)
我爱读游记。小时候,爱读的是郁达夫写的富春江游记,着重文章要写得美。年事稍长,不大看那类散文诗式的游记了,而喜欢写当地风光和人物实况的一类。到了老年,也许是随着身上抒情气质的隐退吧,更是把兴趣转向写得具体、实在的一类。仅仅写进了什么饭店还不过瘾,最好还写点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味道如何,价格如何。如果写旅店,还希望看到房间里有无单独浴室,有无彩电,同时也关心房价和要不要小费之类的事。还有就是人,希望游记作者写些所见的人,他们什么样子,谈些什么,玩些什么。这类游记不是旅游手册所能代替,因为一写人和人的活动,就需要有观察力、同情心和好的散文——只不过好的散文从来不是职业作家的独占物,各界都有能文之士。最近重温两本英国游记,对英国国内的变化和英国散文的变化,都有点体会,写在下面。
这两本书一本是普里斯特莱的《英国纪游》(一九三四)。J. B. 普里斯特莱是一个多面手: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文学史家,二战时期有名的广播评论家,而且在每个领域都做得很出色,他的长篇小说《好伙伴》就是许多人喜欢的,其中写一个戏班子上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演出的情况,就有游记的成分在内。现在这本《英国纪游》是他在一九三三年在英格兰境内旅行记实,行程从南到北折东,然后回到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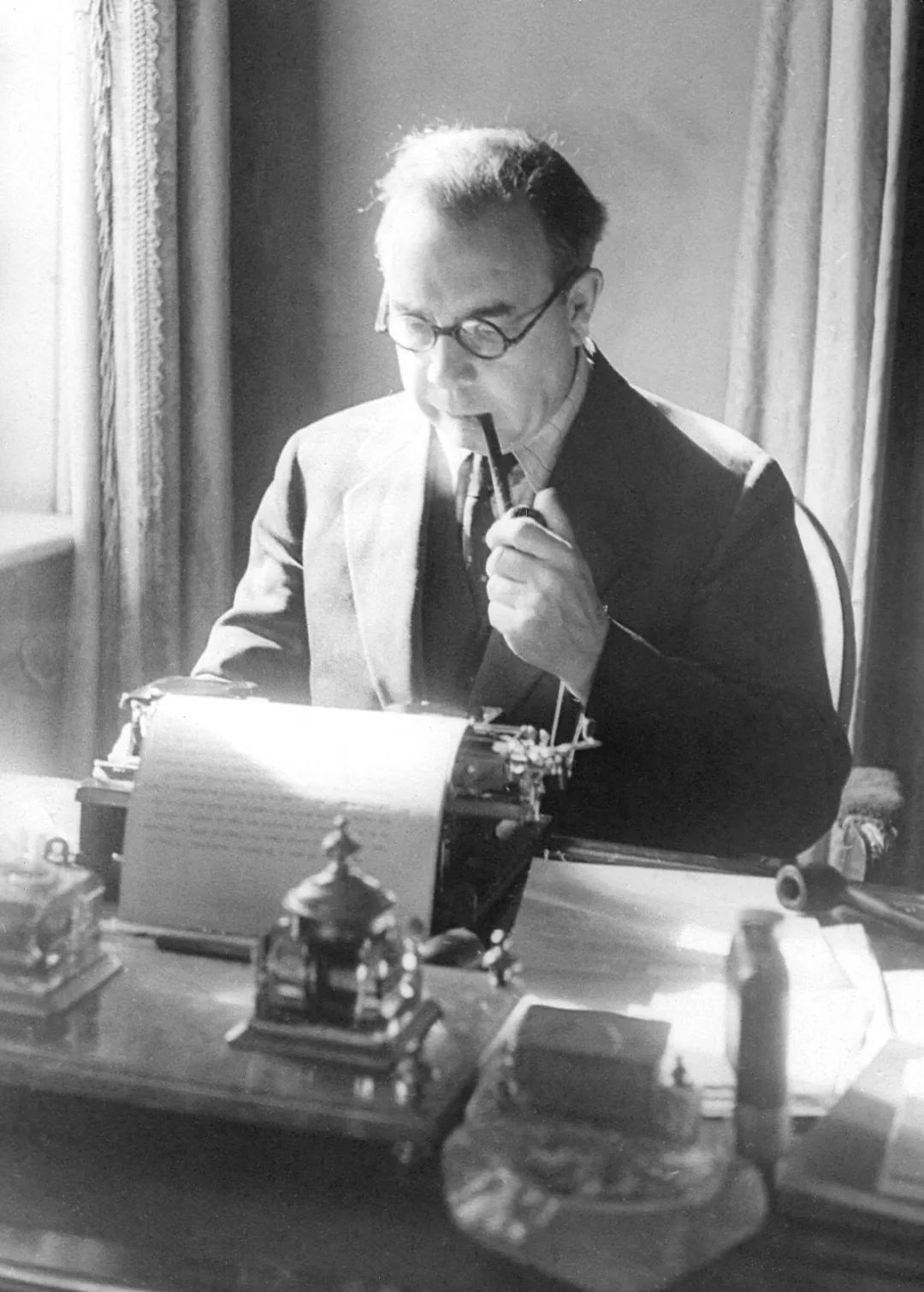
J. B. 普里斯特莱(J. B. Priestley,1894—1984)
这正是英国经济大萧条的日子,生活的艰苦处处可见。再加上早期工业革命留下的疮疤,于是在谢菲尔德附近就出现这样的景象:
我看见一排尖锥形小山,以为是一种怪形的地貌,走近一看才知它们是一个老炉渣堆,不过完全被草盖住了。再过去,又经过一座山,它像是从别的星球搬来的。除了低斜的阳光所照处涂上了一层金色,完全是黑的,布满了深深的伤痕和裂缝。即使在穿过美国内华达州的山区时,虽然那里的景物只是古地质遗迹,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荒凉的山。当然,这不是大自然干的,因为这山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炉渣堆,我所见的最大的一个。
而人的情况呢?普里斯特莱在他的家乡布拉德福特参加了一次一战中老兵的团聚,发现昔日出发时群众欢呼相送的战友们现在处于困境:
而在一九三三年的现在,他们甚至不能到这酒店来同我们喝一杯酒,因为没有象样的衣服可穿。对于死者,我们可以为他们的悲剧而饮;可是对生者的悲喜剧,我们却只能面面相看,感到可怜的难堪;他们为世界而战斗,而世界却不要他们了,结果他们回来脱下军装,却只有破烂可换。谁能追回他们失去的青春年华?
然而这情况之所以触目惊心,还因为英国原是那样美丽,人民又是那样勤劳、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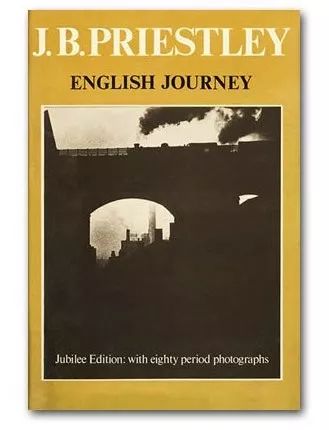
《英国纪行》(Univ of Chicago; Subsequent edition, August 1, 1984)
普里斯特莱是带着异常珍惜的心情写下他所现的风景人物的:
路上有几处可爱的村子。其中之一,名叫勃顿主教村,给了我最迷人的一瞥:一个池塘,几处旧墙,一堆红瓦顶。一下子我就像在那里安居下来了,不问世事,只是勃顿主教村一个爱读书的隐士。
头上是一片晴朗的天,但下面却有极薄的雾丝笼罩了一切,使得山、树、墙都有一种纱巾般的光泽,其虚幻与动人宛如舞台。在这个山谷里有一所孤屋,一座老教堂,还有那我们要去的庄院,它们连接起来,古老的瓦屋顶可爱地挤成一堆。
在却斯透菲尔德城,他第一次看清了那里的钟塔:
我常从火车里注意到它那有名的歪塔尖,但从来没有走近看过。它是叫人吃惊的。首先,比我想的要大得多,实际上高达二百三十英尺。其次,歪得怪,又弯又扭,是英国最奇特最滑稽的塔尖。它镇住了整个城市和城里狭窄的街道,但用了它独有的离奇方式,像是永远在天空安上了一个极大的古老怪物在开人玩笑。生活在它的阴影里的人应该不同寻常,应该到处飞跑,像老勃鲁盖尔的迷人的图画里的小精灵似的市民和农民。
令人神往的往往就在令人憎厌的后面,这是英国的现实。普里斯特莱这样写他的故乡:
布拉德福特是一个完全没有趣味的城市,虽然不完全丑恶;它的工业是黑色玩意儿;但它有好运气,即边上就是英国最动人的乡野。从不止一条电车线的终点只要快走不到一小时就可使你进入荒野,真正荒凉的原始高沼地,这时什么厂房和货栈都看不见了,整个城市也完全忘了。不管你在布拉德福特是多么穷,你永远不需把自己关在墙内,拿砖包围自己,像一百万伦敦人所不得不做的那样。那大块荒山,上面和背后都是一片纯净的天,总在那里,等候着你。而在它们之后不远,真正的溪谷地带开始了。在整个英格兰,没有比这更好的乡野了。……对这乡野的热爱你很小就传染上了,以后也永不消失。不管你的办公室或库房是多么小,多么黑,在你的头脑里一个地方总有这大片高沼地在闪闪发光,总有麻鹬在叫唤,而那里的风是咸味的,像是直接从大西洋中间吹来的。……

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斯陶尔山谷和秦德翰村》
我们去到伊尔克莱,接着通过波尔顿树林到达朋索尔和格拉星顿,从来没有看见那片地方如此奇美。由于刚过去一个长长的干燥的夏天,这一带秋色之美令人难信。整个早晨像在燃烧。干燥的蕨和石南在山顶闪闪发光,码头旁的密林一片斑斓。树像是对我们滴下金子。向下看,赤褐色的树一行一行直到绿色的河边。向上看,荒原高地一片发亮的紫色,叫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我们坐黑牢十年,刚被释放,我们眼见的世界也不可能显得比这里更大胆又更细心地用颜料染过了。我从未见过波尔顿树林如此景色,也不敢奢望以后再见。整个儿是一个盛大的狂欢节,在我有生之日将永在我的记忆里色彩缤纷,闪光发亮。
不止写景,还写人,特别是乡下的手工匠人:
垒墙的,制陶器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又是深谙本行秘密的艺术家。普里斯特莱也曾被制陶用的粘土所吸引,坐在一个旋盘边想自己动手做一个盆子,但是不成。原来他从来不是一个会用手的人,而身边的工匠则个个从家传、从长远的实际经验里学会用手,熟练地爱抚地,拿起一块石头“犹如女人抱起一个婴孩”那样地充满感情。
他还在许多别的地方——往往是被人遗忘的角落——碰上许多这样令他钦佩的工匠,工人,老百姓。他们都忠于所业,以做好工作自豪,但又有强烈个性,甚至显得怪僻,在气质上代表着“欢乐的老英格兰”。而他所见的所谓新英格兰则使他感到沮丧:
我不能不感到这个新英格兰缺乏个性,缺乏热情,生气,味道,辛辣,劲头,创造性,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
这也许可以说是普里斯特莱的旅行小结了。三十多年之后,英国城乡又呈现什么景象?我们不妨来读读另一本游记,即约翰·希拉贝的《穿越不列颠之行》(一九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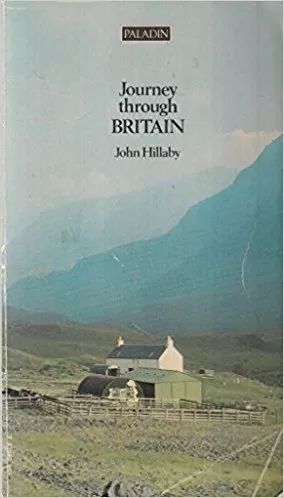
《穿越不列颠之行》( Paladin, 1970)
这本游记除了时间比普里斯特莱晚了许多年,还有其他特点:
一、作者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科学家,主要兴趣在生物学和古生物学,写过非洲游记,并为《新科学家》《卫报》《纽约时报》等刊撰稿;
二、他靠步行周游各地,不利用任何交通工具,所记带有泥土气息;
三、他旅行的范围比普里斯特莱大,不止英格兰,还到了更北的苏格兰等地区,从最南的“地尽头”(Land’s End)一直走到最北的“约翰·奥·格罗茨”(John O’Groa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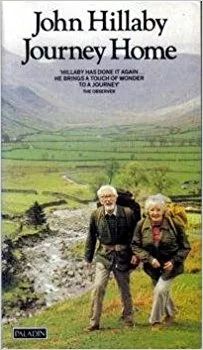
约翰·希拉贝《回家之旅》( Paladin; New edition edition, May 9, 1985)
由于是步行,他有通常乘车的旅行者所没有的经验和体会:脚下土壤的硬或软,岩石属于何类,各种树木花草的特点,小镇小村的建筑样式,每个地方老百姓的脾气嗜好,等等。他看到了走马观花的人看不见的风景。他喜欢河流,常常沿河走上多时,想要弄清它们的源头和去向。特别是康华尔郡的一条小溪,他把它当作旅伴:
向南走,有大片大片的荒野。作为旅伴,我选择了康华尔郡最迷人的一条小河,它是福维河的源头。好长一段时间,这条小河在我前面流着,喁喁地诉说着不知什么,我想什么它也随和地想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旅伴。
走在一片片的白屈菜和银莲花之间,那天早上我有一个高兴的想法,即这条小河是一个小姑娘。她轻轻跳过小瀑布,沿着大石头的边上流,在有白桦和柳树垂下枝叶的深潭里照自己的面容。在哈罗桥她显得不那么妩媚而有点沉静了,像是意识到那里的钓鱼俱乐部的人有权来戏弄她似的。
不止恋河,他也爱山,经常攀越大岭,在山头观看道路来去的形势;不止走在如画的英格兰各郡,还跑到英格兰、苏格兰交界处的古罗马军筑的长城,发现他们垒的石头今天还是十分坚固;也不止是追寻古迹,还注意今天的“边境”风光:
“边境”很美。我想不到有任何别的词儿能抓住这里的开朗气象。村子显得整洁。山上略有不密的梣树和山毛榉,有条条泉水流下,汇集在淡黄色的杰特河,它是屈维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姑娘们也美。在远远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在大北公路上,站着两个带衣箱的姑娘。她们穿着你想不到的紧身毛衣和超短裙。一个当地人说她们“只是两个小婊子”,在等着开远程的卡车司机。尽管这样,她们看起来还是美的。
他有极好的兴致,一天又一天地享受到露宿的乐趣,高高兴兴地上路:
我醒来感到轻快如一只鸟。有点薄雾,看不清远处,但不打紧。景色好,感觉好,气味也好——一种混合着泥炭和青苔、来自土壤的最纯净的空气的味道。
有时露宿之后,他就脱了衣服在草地上一滚,让露水代替了淋浴。有一次因为天热,又正走在四顾无人的荒原上,他索性赤身裸体行走,不料一个年轻女人骑马经过,他赶紧躲在野草丛中,才算没进警察局。他也常常碰上下雨,好几次淋得透湿,有一次避雨所在正是小说家勃朗蒂姊妹常去漫步的约克郡荒原。由于不断步行,皮鞋掉了跟,鞋头断了线,碰上好心人指点才找到好心的鞋匠,几分钟就把鞋子修好,却不要他一个钱。同样地,有一次他饿极了,也碰上了好人:
密特·考尔徒的乐善好施者原来是一位青年工程师,他正忙于为他妻子的理发馆的大门上漆。他说“也许可以找到人”,但觉得应该先打一个电话。他找的人,其实我应该猜到,就是他的妻子。他俩邀我到他们家去,就在附近的住宅区里。我在那里吃了大量食物。他们有点出乎意外,但很高兴,把柜里剩下的东西全都搬出来让我吃。第二天早上我要付钱,那男的只摇头,他的妻子——一个非常美的女人——用手挽住我的脖子,吻了我,热情地。
他的观察极其细腻,如这样写鸟:
不少鸟有我们所谓的优美风度。为了生存的必需,它们注意使自己的飞羽保持完好无缺,爱护身体的每一终端犹如小提琴师爱护自己的手指。不妨看看鸥和一种相近的鸟,叫做鴴,它们会作一种独特的体操。在空中它们同风玩耍,逗乐,翻来滚去,显然不在乎大风怎样朝它们劲吹。但一等不飞了,就滑翔而下,轻轻落脚,似乎不触及地面似的,一阵小跑后停住了。有一瞬间它们把翅膀张开,向后一掠,形态如作一侠士式鞠躬。然后它们带着一种极乐的颤动在鸟巢上安定下来。阿尔陀·利奥波特说:发明“优美”这个词的人一定看见过鴴的收翼动作。
由于是步行,他比乘车的旅客更能实地观察生态环境。使他痛心的是,美丽的英格兰正在遭受人为的生态破坏。在英格兰北部,有一个群山之间的小盆地,叫做考·格林,长着许多稀有的植物,“植物学家珍惜此地超过北英格兰任何别地”,可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 C. I. )为了制造一种肥料缺水,要求把那块盆地筑成一个水坝。热心于保持生态的人反对此举,向政府告了状。希拉贝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政府尚未裁决,但等他来写这部游记,事情已经无可换回:
考·格林事件已经结束。虽然英国每一个有名望的生物学家都反对这个动议,政府却退缩了,批准了筑坝的计划。这个山谷将被水填满。
政府如此,当地居民也不管生态什么的,他们希望的只是能有“更多的买卖”。而主管生态环境的人则只是一些官僚:
在英国,掌管生态平衡的是组织者,他们圆滑,谨慎,想的是委员会。
历史上的人为灾难也使希拉贝感慨不已。他走到苏格兰西部高原,看到了一些“无人遗址”:
在整个西部高原,许多居民点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些被砸了的家屋遗迹称为larach,字面的意义是“遗址”,表示曾有屋子而现已无存。一次又一次我出发去找一个地图上有的地点,希望至少能找到一间草屋,却只见一小堆石头或者——在格兰勃河附近土质较好的一处——连石头也没有,只有一丛荨麻。别的什么都被拉走了。“遗址”是高原最可怕的事件的见证,即“清地”。
这种“清地”的实况是有目睹者的记录的。希拉贝在他的游记里引用了一些:
我紧跟斯特拉司内弗上面的小路走去,那里有一条产鲑鱼的著名河流穿越一个名声极坏的山谷。
在这里苏索兰伯爵一家火烧了不肯让地给羊的长期佃户的家屋,用这个办法增加了收入三倍。……
唐纳德·麦克略德,一个当时的本地石匠和事件的目击者,说“每区都有一群强人带了柴和别的易燃品,冲到这些忠心的人的屋子,立刻把它们点上火,用最快的速度来干,大约三百所屋子成了一片火海。人们极度恐慌,混乱。几乎不给任何时间让人把人和物移走,住户只好挣扎着先抱出病人和不能自理的人,再抬出最值钱的东西。浓烟烈焰中女人和孩子哭成一片,看羊狗吠叫着赶牛,牛大声鸣吼,整个情况完全没法形容。”
特别是有关一个年近百岁的老奶奶的一幕:
在那已成为斯特拉司内弗的可怕历史的一部分的报告里,唐纳德·麦克略德说道:“我对那些要对她的屋子放火的人说了情况,总算使他们同意等到管家撒勒先生来了再说。撒勒一到,我就同他说可怜的老太婆由于身体情况无法搬动。他答道:“该死的老妖怪,她活得太长了,让她烧死。”房子立刻点上了火,人们抢着把她裹在毛毯里抱了出来,但是毯子已经在燃烧了。她被放在一个棚子里,人们尽了最大的力才使他们没有把棚子也烧掉。老婆子的女儿赶来了,屋子已经在烧,她帮着邻居把母亲从烟火里救了出来,情况太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没法说清。五天之后她就死了。”
真是令人不堪卒读。但这也表明:这本游记是大有内容,很值一读的。 
等我们冷静下来,也许会问:除了英国国情的不同,是否也可以通过这两本游记看一看三十多年里英文散文有了什么变化?
比较在这里未必能有多大意义:材料不多,作者各异,限制性相当大。但又不妨一试,因为在有限的范围里,分别还是明显的。两人去了不少同一地方,甚至注意了同一现象,例如都看到了垒墙这一快失传的手艺,写法却不一样:
普里斯特莱写了长长的一段:
我被介绍给老乔治,一个考茨物尔特的石匠。他已年过七十,但仍在干活。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在干一项快要失传的手艺:乾垒,就是把快塌的旧墙推倒,用它们的材料重垒平整坚实的新墙。他是小个子,有一张满是绉纹的土灰色的脸和一个极大的上唇,看起来像一只有智慧的老猴子。他长长的一生都同石头打交道,身上到处都有小石头。他摆弄身旁的石头——还拿出了几块让我们瞧——那轻松、爱抚的样子就像女人抱婴儿似的。他本人就像是从石头生出来的,一个石矿的精灵。这位老乔治又是虔诚教徒,不谈石头的时候就用一种安静然而充满热诚的态度谈他的古老、朴素的信仰。由于是一个真正的工艺能手,知道他能干出你我干不出的绝活,他显然喜欢他的工作,不是为换得几个先令而付出劳力,干活是他自己完整个性的表现,是一种记号,表示老乔治还在干着。不好的墙——不是他垒的——在倒塌,好的墙在树起,墙上的石头垒得又结实又平整,看起来愉快,心里也满意,不是那种讨厌的糙工次活。我一生里从未做过一件事像这位老石工垒墙这样的彻底和真纯。
希拉贝却只三言两语:
干垒的老手艺正在死亡。这行业的本领在于用长条石板(称为“通板”)把两层粗砂或石灰石横向垒紧。奇迹在于用这种不稳当的办法居然做到了长远的稳固。
应该说,两人写法也有相同处:文字都是平易的;两人的感触也相同:都在惋惜这一古老手艺的正在消失。但更显著的是不同:文学家普里斯特莱像写小说似地描画了一位老匠人,而对于这手艺本身只说了一句话:“墙上的石头垒得又结实又平整,看起来愉快,心里也满意,不是那种讨厌的糙工次活”,而这句话里也是感情渲染多于具体描写,“实”的东西不多。希拉贝看起来写得简单,字数不到普里斯特莱的五分之一,然而却写得实在,细节分明。他也有感触,但溶在描述之中,只用几个词就画龙点睛(“死亡”,“奇迹”,“长远的稳固”),写物实亦抒感。毫无疑问,普里斯特莱是善于用笔的,但是他的许多感想是比较空泛的,可以预料的(“爱抚像女人抱婴儿”之类),说得太多反而给人以“做文章”的感觉,因此相形之下,希拉贝的科学家的确实和经济反而显得新鲜了。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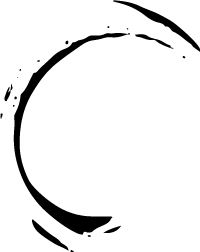
其他精彩文章

“读书文丛”(精选)之王佐良《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